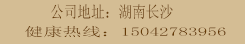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食人鱼 > 食人鱼的生活环境 > 亚马孙探险,为何令人心驰神往
当前位置: 食人鱼 > 食人鱼的生活环境 > 亚马孙探险,为何令人心驰神往

![]() 当前位置: 食人鱼 > 食人鱼的生活环境 > 亚马孙探险,为何令人心驰神往
当前位置: 食人鱼 > 食人鱼的生活环境 > 亚马孙探险,为何令人心驰神往
文
潘沙
潘沙,文史学者,主攻西洋史与文化史。
刚愎自用又疑神疑鬼的领队、干练精明又为情所困的探险家、自告奋勇又力有不逮的赞助人、沉默寡言又忠于友情的独木舟手、胆大心细又不谙荒野的女医生、无备而来又嗜好冒险的记者……一支从五湖四海凑起的“杂牌军”,顺着亚马孙河的源头,跨过雪域与密林,向大西洋跋涉,等待他们的是厄运还是传奇?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亚马孙令人魂牵梦绕,它的魅力源于口耳相传的神秘故事或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本能?《航向亚马孙》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答案,却能带你探索未知。
征服者、黄金国与女武士传说
亚马孙进入欧洲人视线,始于黄金国传说。皮萨罗兄弟用诡计擒住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获得一屋子黄金后,贪心仍难满足。被搜刮殆尽的印加人放出风声,在美洲大陆腹地的丛林里,存在一个黄金满地的国度,富庶得无法描摹。
为了防止同胞或政敌捷足先登,担任基多总督的冈萨罗·皮萨罗匆忙组建一支远征军,他麾下的得力干将就是弗朗西斯科·奥雷亚纳。远征军由个印第安人与个西班牙士兵组成,跟随他们左右的是上千只猎狗。在崎岖密林里,猎狗充当开路先锋,食物匮乏之际,它们就悲惨地沦为了盘中餐。这一招,被三百年后的刘易斯-克拉克远征队学会了,至今美国人还对此津津乐道。大军推进到亚马孙水系,人困马乏,猎狗也大多进了肚子,皮萨罗只得派出奥雷亚纳作为先遣队继续深入丛林。
孰料,先遣队在几天后音讯全无,皮萨罗被迫收拾残部勉强爬回了基多,向国王写信汇报奥雷亚纳的叛逃行径。其实,奥雷亚纳小分队只是遇到了意外,他们在湍急水流里向下游漂了足足数百里,到了一片陌生之地。在土著人的一番款待后,他们重新上路,却遇到了另一伙不算友善的土著人。仗着火力优势,西班牙人幸免于难,却在慌乱里漂流到了更远的下游。他们的逃生之路,没有《航向亚马孙》里探险旅程的从容不迫,更类似于柯南·道尔小说《失落的世界》里的仓皇失措。
收整兵马之后,难知归路的奥雷亚纳已经置身于亚马孙干流,他索性完成了一场雨林考察。他最大的收获,乃是一场遭遇战,奥雷亚纳与一群长发土著人短兵相接,他想起了希腊神话里女武士亚马孙的传说。交战过后,他四处搜寻女武士的痕迹,听闻丛林深处确有一个女儿国,那里的人们浑身珠光宝气,用黄金碗吃饭。奥雷亚纳从雨林逃出生天之后,“亚马孙”的名字不胫而走,沿袭至今。
在现代语境里,西班牙人以女武士命名河流,不免被怀疑有着征服色彩,一如日后南美流行的探险家与女奴的爱情故事。不过,亚马孙无疑是狠角色,不是低眉顺眼的女奴。希望在寻找黄金国途中征服河流的人不计其数,成功者却不见踪迹。葡萄牙军官佩德罗·特谢拉、传教士萨缪尔·弗里茨、博物学家何塞·阿科斯塔都步了奥雷亚纳的后尘,追索女武士传说。特谢拉划着独木舟从亚马孙三角洲逆流而上,一路宣布两岸土地归葡萄牙所有,大摇大摆抵达西班牙人控制的基多,可谓余勇可贾。
在寻找女武士与黄金国的时代,最灰头土脸的,要算英国著名海盗沃尔特·雷利。在对西班牙海上作战立下赫赫功勋的雷利,在殖民地却颇不得志,他建立了弗吉尼亚,但经营不善,颜面尽失。为了重获女王信任,他从圭亚那登陆,踏上寻觅黄金国之路。剑指亚马孙的大海盗,在奥里诺科河就裹足不前,折损半数船员,探险失利让他身陷囹圄,最终被架上了断头台。
科考者的乐园,探险家的地狱
近代以来,足迹抵达南美的科学家里,最著名的当属亚历山大·洪堡与达尔文,可惜两人都不曾深入亚马孙腹地。尽管如此,亚马孙还是在一片喧嚣里,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乐土。
亚马孙流域的科考先行者,是18世纪中叶的法国人拉·孔达米恩。他原本前往基多测量赤道,好奇心促使他带上弗里茨的地图,跨过安第斯山,沿着马拉尼翁河向下,直达亚马孙。《航向亚马孙》里探险队的行程,大致也是承袭了他的路线。拉·孔达米恩为欧洲带回了两样宝贝,橡胶与金鸡纳霜,前者为工业时代提供了韧性,后者救治了无数疟疾患者,康熙也是获益者之一。
拉·孔达米恩探险队的传奇还未结束,他手下的数学家戈丁,与一位委内瑞拉姑娘结婚了。忍不住思夫之苦的戈丁夫人,带上几个随从沿着亚马孙河航行,谁知遭遇船难。身边的人相继死亡,戈丁夫人只身穿过险滩与急流,在印第安人帮助下,走出了丛林,与阔别二十年的丈夫重逢,不禁令人感叹爱情的伟大与生命的坚韧。
与一心寻觅黄金的伊比利亚人不同,19世纪亚马孙流域活跃着很多醉心科学的英国绅士,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是个中杰出代表。后世听闻他,大抵源自科学史上那桩知名公案——进化论提出者之争。达尔文赏识才华横溢的后辈,却被许多批评者扭曲为他的毕生污点。抛开公案,华莱士在亚马孙的生物学贡献足以令他彪炳史册。他与好友贝兹、斯普鲁斯一道采集了数量庞大的珍稀标本,本应掀起一场生物学革命。谁知,他的心血,毁于归途轮船上的一起火灾。冥冥之中,前不久,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大火,又将华莱士同代人辛勤收集的另一批标本付之一炬。
若仅以名气而论,有一位亚马孙探险者丝毫不输给洪堡与达尔文,他就是跻身美国总统山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卸任总统后勇闯雨林,这份胆识不逊于他在美西战争里家喻户晓的战地冒险。亚马孙不在乎来者的名气声望,罗斯福在密林里脚部受伤化脓,高烧达到40度,在绝望里他曾叮嘱同伴把自己留在原地,以免耽误求生的机遇。好在他的同伴没有让美国总统自生自灭,搀扶他走出了险境。
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个冒险家珀西·福西特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他真的在亚马孙上了天堂。他曾为皇家地理学会测绘巴西、玻利维亚与秘鲁的边境,自此与雨林结缘。在印第安人中间,他听说了迷失之城的传说,决心深入亚马孙让它重见天日。在他写给妻子的信里,福西特透露,在死马营地枕戈待旦的他,将要搜索印第安人口中恐怖的古老石塔。据说,入侵者降临之时,石塔深处会射出光芒。在可怖传说的迷雾里,福西特失踪了,他的故事在近百年后被拍成了《迷失Z城》,令亚马孙爱好者悸动不已。
说句题外话,《航向亚马孙》里提及了伊基托斯的中餐馆,也是这一时代形成的。在密林深处,华人拓殖者辛勤耕耘,充当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协调者,为亚马孙开发默默奉献了数十年。
忧郁的热带:亚马孙之古今变迁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经典之作《忧郁的热带》开篇如是写道,不难相信,几乎所有的探险家与人类学家都在著作里有类似的口是心非,亚马孙探险也从来不是一件名利双收的轻松差事。
《航向亚马孙》里,乔·凯恩所在的探险队与19世纪的前辈大相径庭。伊比利亚征服者的眼里满是黄金与肉桂,华莱士与贝兹既心存科学又幻想科学背后的功名,现代探险队则怀揣创造纪录的野心,希冀着可以贩卖给出版社或电视台的非凡经历。他们是幸运儿,虽然队员不停抱怨真空铝箔让食物味同嚼蜡,但他们能吃到米饭、马铃薯、酸甜虾、勃艮第酱汁牛肉与意大利酱汁鸡肉。
19世纪探险者所炫耀的征服自然壮举,几乎全部是在印第安人的协助下完成的,尽管他们在游记里的戏份都不算多。由于现代道路与车辆强大的补给能力,印第安人用高椅背着探险家翻山越岭的尴尬场景一去不复返,尽管在攀爬高山之际,土著向导的经验与古柯叶始终不可或缺。同样拜现代技术所赐,他们也有更便捷的通讯手段,不再需要在大城市苦盼家书。不过,这也为他们带来困扰,不安分的世界总在警醒着旅程之外的牵绊,严格执行宵禁的秘鲁海军、开普敦黑白斗争时代的爆炸案与风云诡谲的波兰政治让队员分心,探险主心骨赫梅林斯基为与波兰女友的团聚揪心,乔·凯恩则为离世的叔叔和罹患癌症的姑姑神伤。
亚马孙之于探险者,并非亘古不变,正如书里所言,丛林每天都需要按照人类的秩序和命令,或依据人类的幻想,被改变、规范或训诫。他们见证了许多戳破田园牧歌之梦的细节,譬如,除了主教与卡斯特罗,在秘鲁乡村最受欢迎的形象是米老鼠。可是,美国制片商想在一座草桥取景,一旦价格没谈拢,当地居民竟然一把火将桥烧了。又如,在秘鲁的沼泽里,路遇一个弹吉他的小孩,叫做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毋庸置疑,秘鲁的亚马孙地区抵挡不住现代文化的侵袭,但当地人对美国却怀着痛恨之心。乔·凯恩是个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混账”“英美佬”是他一路上时常享有的“尊称”。一个关心政治的秘鲁朋友为他讲起一个绝妙吐槽——“在我们秘鲁,扯一头黑牛的乳房就有咖啡,拉一头白牛的乳房就有牛奶,如果去拉它的尾巴,就会惹来一脸的牛屎:我们把咖啡喝牛奶卖给美国,自己吃牛屎。”
现代探险,颠覆了不少刻板印象,其中不乏《狂蟒之灾》《夺宝奇兵》之类大片框定的成见。乔·凯恩着墨的重点,在秘鲁而非巴西,这不意味着巴西的亚马孙水系波澜不惊,至少对独木舟漂流而言,上游的秘鲁山区更为惊悚。探险队员一路上小病不断,却没遇到太多致命挑战,许多丛林疾病可以通过现代疫苗预防。在凶险的水域里,他们没遇到食人族,独木舟下也没有蓦然冒出一群食人鱼。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手上都没有像样的武器。
旅途的尽头,是自然还是自我?
当然,一些自古以来令人挠头的难题无法回避。亚马孙河并不温驯,它会“在无预警的冷酷中,把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爱、所乐或所恨完全摧毁,也就是以简单而令人悚然的夺命方式,完全将一个人周边的宝贵宇宙,从他眼前席卷而去……”在旅途中,他们也遭遇了人类文明的古老命题——民主或专制。早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就曾借波斯人之口探讨了这一伟大命题,但当领队奥登达尔与主心骨赫梅林斯基意见相左,队员面临着艰难选择,一直告诫自己冷眼旁观的乔·凯恩也被卷入其中。要命的还有赞助人杰根森,没人想把下金蛋的鹅赶走,但他也可能将全队拖向深渊,这一幕与电影《迷失Z城》的情节如出一辙。
归根结底,乔·凯恩笔下的探险奇遇,精彩不止在于古今异同,更在于形形色色的人。奥登达尔面目可憎,却是探险发起人,又是难得的鼓吹者,筹措资金全靠他的努力;赫梅林斯基沉稳自律,却蕴藏着可怕的火气;开心果本兹岱克、冷峻专家特鲁兰、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比格斯、仅有的巾帼达兰特等等,都在探险队扮演着不同角色,也让此行前所未有的生动。19世纪的游记里,孤独行程、沿路食宿与珍奇动植物描绘占据了大半篇幅,但乔·凯恩更擅长写人的冲突与妥协。更何况,探险队的路途并不孤单,他们邂逅了随意射击的光辉道路游击队,“河上没有别的船,而他们有枪”这般鸣枪理由,充斥着南美式黑色幽默。他们还遇到了殷勤淡定却不当面骂老婆的印第安人、热情过度的麻风病人、调戏巴西人只会“跳舞和做爱”的边境军人以及酷爱喝酒、抽烟、睡大头觉的船长。在他们的陪伴下,漫长艰辛的旅途妙趣横生。
但乔·凯恩的旅途里,不只有与行色匆忙过客的插科打诨,深沉思考俯仰皆是。在自然与旅伴之外,穿越亚马孙的路上,最难对付的其实是自己。他引用前人游记,写道:“旅行的当下,其实会使一个人的视界变得狭小,因为每天所专注的事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找食物,以为找地方住……”不消说远途冒险,对于普通游客,如你如我,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完美的旅行只存在于回忆里,而路途里只有疲倦、奔波和对下一程的忧惧。
在倦怠之余,拖着人们前行的是成功欲。对探险者而言,人人都被斯科特的故事打动,但人人都想做阿蒙森。与此同时,对自然的敬畏从妥协变为信仰——与自己为敌,与自然为友,逐渐悄然成为一种主旋律。在一次侥幸逃脱激流后,在亚马孙流域经验最为丰富的赫梅林斯基一语道破探险真谛——河流永远是赢家,它才不在乎再多赢一次,我们尝试泛舟,是因为我们必须一试……
原载于《南方周末》年11月8日C28阅读版
长按识别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renyua.com/tgfz/7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