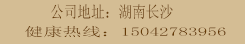?GilbertGarcin“你好。”我正在公寓楼前清点家中旧物,一个从没有见过的男人向我打招呼。他的那一身黑衣与现在的天气很不相称,但必须承认,他的黑色羊绒外套和毫不染尘的灯芯绒裤子很考究,手工的布洛克皮鞋油光锃亮。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这样一个穷得要烤老鼠来吃的街区,打算做什么。他看见我在打量他,礼貌地摘下手上的小羊皮手套,和头上的黑色礼帽,漂亮的卷发和修剪整齐的髭须让他瘦削的脸显得平和沉稳。他冲我露出友好的微笑,我通常只有被抢了钱,对方对金额感到满意时,才能看见这种笑容,至于他的那口白而亮的牙齿,至少在这个街区,见所未见。一个20世纪的英国式的绅士,出现在21世纪的穷苦街区,他不仅来错了地方,还来错了时代。“你想干嘛?回到未来吗?”我拄着旧立柜问。“不是的,先生,我是一名推销员,您或许会觉得我的服装不合时宜,对于现在的天气来说,是太热了些,但因为我推销的产品非常特殊,为了取信于人,减少说明的难度,使顾客第一时间就能够明白产品的用处,非如此打扮不可。”“就是你推销的东西很扯淡,你穿这么扯淡,再说扯淡的话,就没人揍你了,是这意思吧?”他从马甲背心的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说:“您这样说,也无不妥,不过使用暴力毕竟……毕竟是不提倡的。”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位《万能管家吉尔斯》似的人物,看他局促、紧张,不过是一个刚入行的生瓜蛋子,不想再搭理他,还有活儿要干,于是摆摆手,示意他走开。继续干我的活儿。在夏日的烈焰中行苦役,并非是出于磨练自己的意志,或宗教修行的需要,完全是因为我的老婆,一个该死的、挨千刀的女人。在婚姻之初,她是一个体型纤弱、沉默寡言的姑娘。生活的折磨赋予她更坚强的胃,更极端的情绪,和更糟糕的脾气。不过是怀疑我在酒吧和别的女人多说了几句——我承认回家是晚了点,她就拎着斧头劈开了每一件家具,像劈开被雨淋透的南瓜——或者我的脑袋。她将惊喜留给喝了六瓶科罗娜啤酒和四杯螺丝刀的我,带着现金和几件首饰扬长而去。最让人恼火的部分并不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而是现在。我把烂木头搬出来,为了让它们发挥余热而绞尽脑汁。或许,可以做几件木雕,带点非洲味儿,多贡族的阿玛、卢旺达族所的伊玛纳、马赛族的恩克艾、贝宁族的马武利扎,随便什么。收拾木屑就不太容易,我把吸尘器开到最大档位,用胶带粘,用软毛刷细细清扫,只能放弃。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做完这一切,我得去把她找回来。如果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就好了。她消失在夜色里,消失在屎尿遍地的后街的污水里,消失在夏天的虫鸣声中,该有多好。但我知道,这就是问题。而如果我不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她的娘家或朋友家,她就会像突然来临的风暴,砸碎每一扇窗户,每一个杯碟,每一处墙壁,用震耳欲聋的声音质问我,为什么不去接她。去死吧。我直起腰,想至少犒劳自己一瓶冰啤酒,余光扫过,那抹黑色就佇立在路灯下。我看向那个怪人,他还以微笑,并脱帽致意。“K,这是你的相好吗?你这个异装癖变态。”H骑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自行车生锈的部分发出噪音,但他的声音比噪音还让人难以忍受。“去你妈的,狗杂种。”我啐了一口。那个怪人还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脸上的笑容像冻干草莓。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装扮,他却没有掏出手帕擦汗,他是退伍军人吗,我猜测。我走到门口,又拐回来,“喂,你,喝啤酒吗?”“喝是喝的,但是酒量不佳,所以不多喝。”“科罗娜?”“虎牌。”“进来吧。”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起居室现在的样子,他们多半会怀疑几个小时前,FBI在这里和一伙毒虫发生了激烈枪战,虽然使用的是5.56毫米的制式武器,但一方财力雄厚、储备充足,另一方有纳税人,子弹像堆在超市后巷的过期食品,没有死人,却产生了巨量的熵。我忍不住想,如果真的有毒虫和FBI,为什么不先杀了我的妻子。“找地方坐。”我的老式冰箱非常好用,可靠,冷藏室被砍成两半,但冷冻室还能运转,我从里面捞出两瓶半凝固的啤酒,在厨台的边缘磕开瓶盖,将其中一瓶‘虎牌’啤酒递给坐在沙发靠垫上的怪人。我发誓,只要他发表一句关于我的起居室的评论,我就打烂他的下巴。“没想到冻过的啤酒如此美味,清爽得非常具体,感谢款待。”他把礼帽脱下,捧在左手里,欠了欠身,用右手里的酒瓶和我碰了杯。“喜欢东方?新加坡?”“日本,麒麟和朝日啤酒难得一见,在外只说自己喜欢虎牌。”“去过?”“你喜欢日本女人吗?”我笑了笑,“没有人不喜欢。”他也微微一笑,问:“可去过?”我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低估了他。“推销什么的?为什么来这个街区。”我指给他看,窗外的不远处,一个吸强力胶的十几岁少年,正在“开宝箱”,他大概是几天没有吃饭了,不得不在垃圾箱里找吃的。这是街道尽头那所垃圾场一样的房子里的长子,我知道他们家是做家具的,劣质家具。其实他不用吸强力胶,甲醛早晚会要了他的命。“我猜他偷了家里的钱,买了点神仙水或者摇头丸,嗨了几天,现在不敢回家。你看他的凹陷的屁股,那条满是疮疤的脖子,这个街区充满了这样的垃圾,你指望在这里推销出什么东西?”礼帽怪人喝了一口啤酒,直起上半身,眉头紧锁,小心拣择词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推销一种将生活中的问题消除掉的办法。”“自杀工具吗?”他愣住了,过了一会儿,笑出声来。我喜欢这个家伙。“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推销的方法,代价可能要小一些”,他解释道,“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将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变成一只宠物。”“宠物?”“对,三花猫、牛头梗、绿鬣蜥。这类东西。当然,奴隶少女之类的,也不是不行,但代价太大,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我还是不明白。”“试过一次就懂了,你有烦恼吗?”我点点头。“恕我直言,阁下的烦恼恐怕不止一处,还请你自己选择。”我指了指那台冷藏室裂成两半的冰箱,“冷藏室坏了,无法储藏啤酒。”他点点头,“这是个大问题,必须立刻解决不可。就这么决定了。”说完,他起身告辞。“这就走?”“这就走。”“不需要费用吗?也不需要任何文书?”那副如同半凝固啤酒的笑容又回到他脸上,“代价是另外的东西。文书之类,不能留下的,你也知晓,我们的方法并不怎么需要法律的保护。”说完,他大步走向走廊,在走廊上直角拐弯直奔房门而去,其动作之迅捷,让我怀疑他并非人类。总而言之,不过是午后的一件怪事。在经历一个下午的苦劳后,我就着牛肉罐头喝了两罐啤酒,躺在满是木屑的地板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见妻子满身是血地坐在过山车上,随着车体转向疯狂地摇头,那样子,就像一具尸体。我是被门铃声吵醒的,没理会。但对方按个不停,我从地板上爬起来,顺手抄起一把厨刀,一把拉开房门。一个快递员快速地朝自己的车跑去,地垫上放着一个纸箱子。我用厨刀划开胶带,拎出一个鸟笼,一只灰鹦鹉看着我,又将头埋在翅膀下,没睡醒似的。我将笼子扔在门口的置物柜上,走到冰箱前,拉开冷藏室的门,拿出一罐冰啤酒,打算边喝边想想今天应该去干点什么。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小毒虫的老爹打些家具,虽然我不想被甲醛毒死,但是,我没得选。等等,冰箱是什么时候修好的?“下午好。”我抬起头,那个怪人又站在路灯处,向我脱帽微笑。“你怎么又来了?”“我来回访客户,请问对冰箱和灰鹦鹉还满意吗?”我放下手里的刻刀,“虎牌?”“当然”,他跟着我一起走进房门。我总算是将起居室收拾出来了,多亏了一张廉价的旧地毯,大到足以盖住地板上的问题,至于在它的下面,是白蚁在啃食木屑,还是一个性能强劲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在偷窥,我统统不在乎。我看着他坐下来,对房间的变化无动于衷,就像上次一样。他的衬衫浆洗过,领子硬挺着,装饰了一条阿拉伯式样的丝绸领巾,猩红色羊毛外套的领口装饰着银质领扣,上面有什么符号,看不清楚。他的白色的制服裤一尘不染,柔软的黑色猎靴像胶皮袜套,让我怀疑他有什么恶趣味。他把猎鹿帽拿在手里,像刚在约翰·桑德森·维尔兹的画里结束一场狩猎活动,而且收获不错。我把啤酒递给他,坐在地板上,决定开门见山,“你是不是在诈骗?”他喝了一口啤酒,“我骗了你什么呢?”“你趁我不注意,换了我的冰箱,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话,你有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方法。”“什么方法?”“把‘问题’从生活中拿出去。不需要更换冰箱,也不需要修它,只需要将‘问题’拿出去,一台‘有问题的冰箱’拿走了问题,就变成了一台普通‘冰箱’,就是这么简单。”“还把它变成了一只动物,比如灰鹦鹉?”他点点头。“无稽之谈,你不如说你可以把我的‘肾’从我的‘身体’里拿出去,这还比较可信。”“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的肾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我看着他,思考究竟该说些什么。良久,他先开了口,“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难以置信。10年前,如果我告诉你只需要再等10年,你就可以在一台手掌大小的电脑上买到你想买到的任何东西,纸币将不再是必需品,人们不再热衷于‘交媾’,他们看看网页,然后把它关了,一整夜都不会看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一眼,连高中生都不再‘敦伦’,就好像他们的青春期被推迟了,而且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你会信吗?”“但是你说的,和科技进步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没什么区别,一间完全不需要开灯的,全部由机器人构成的工厂离你只有不到20公里,一间由性爱机器人服务的妓院就开在市中心广场的一处地下室,三年前,那里是全城最好的酒吧,每个被工作折磨疯了的人都要在下班后,去那里把心里的垃圾倾倒出来。后来,大部分人选择了在家办公,市中心破败不堪,脏得连流浪狗都不愿去。这个时代就像一台巨大的离心机,转子就是科技进步,它运转起来,越转越快,把每一个握得不够紧的人甩到时代的边缘去,你不相信,只是因为开关不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说的像是骗人的鬼话,那么,我可以换种说法。在前年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上,来自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卡特·殊拉(CarterShukla)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描述了他们发明的一种全新技术,即如何理解多元宇宙,并为之分类。以他的论文为基础,应用物理学界很快就诞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现在,我们可以遍历多元宇宙,抽取任意时间线上的任意物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关于你的无数种可能性中,通过概率计算寻找到你的电冰箱没有发生故障的那一种,然后将你的坏冰箱,和另一个你的好冰箱换过来。”“还额外赠送一只鹦鹉?”“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操作的副产品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多出一只动物,另一个宇宙的物质总量减少了,这个宇宙的物质总量增加了,具体会有什么影响,谁也不知道。第一代技术嘛,慢慢就会好的。上次之所以告诉你既不需要费用,也不需要文书,是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这么说,感觉上好理解多了。”“那这么说呢?这是一部真人秀,我负责找到别人的问题,通过各种幕后操作,解决他们,让问题的主人相信他们见到了奇迹,让他们哭、笑、哭笑不得。观众们在屏幕前看到这一切,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居然会有人发愁一台坏了的冰箱——为什么不扔掉买一台新的,有人偷了几十块钱而回不了家——是因为家里从不使用现金,觉得现金更为珍贵吗,有人还在骑一辆上世纪产的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行为艺术吗。他们看到了想象之外的世界,并为此付费。上次来你家的时候,我偷偷扫描了你的冰箱,记下所有的特征和使用痕迹,我们的工程师精心制作了复制品,我们的工作人员又趁夜进行了替换。之所以要送你一只鹦鹉,是因为你一个人生活,我们——我们的观众认为你太孤单了,需要陪伴。而我之所以穿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来自时尚界的广告客户想要让复古的维多利亚式的服装再次流行起来。你的上一期收视率还不错,通过广告植入、贴片广告分成、流媒体平台分成、节目订阅等方式,我们赚回了几万台冰箱的钱。而之所以装得神秘兮兮,直接把你拉进来,一是为了真实,二是为了不付给你任何费用。这么说,是不是更好理解了。”“哪种是真的?我怎么查不到这个什么狗屁教授。”“哪种都不是,都是我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需要故事,随时都有,五十块的故事也有,五百块的故事也有,五十万的故事也有,看你的需要。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那你得告诉我一个尽量真实的,故事。如果你能说服我,我真的有个大问题需要解决,你需要生意,对吗?”他看着我,微笑着,“好吧。你相信语言之外再无世界吗?”“我连这句话都不懂,相信个屁。”“不重要,我们都生活在语言的包裹中,语言构成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存端底以来我们运用语言的方式。只要是语言,就有语法,而偏偏有些力量可以通过运用普遍语法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什么力量?”“锡蒙利、但他林、奥丁、荷米斯、一言主神,随便你怎么叫都可以。”“为什么要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唔,如果你把完善的资本主义想象成所有魔神中最有力量的那一个,那么我想其他魔神所做的事,大概可以理解为战争,当然我不知道阿瑞斯、贝罗纳、门图、塞建陀、内特、涅伽尔有没有参与进来。这只是个故事,不用这么较真,没什么逻辑可言。如果非要编得更圆满自洽,恐怕阁下非要付我千字不少于八百元的稿费才可以。”“动物是怎么一回事,三花猫、牛头梗、绿鬣蜥一类?”“也许是恶趣味,你看过《布拉格的大学生》,一部德国老电影,魔鬼用金钱和一名大学生交换他的镜中影像。可见至少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魔鬼就在做这样的交易了。也许是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体系纳入其中,每个都忙得马不停蹄,在问题解决之后,留下自己的象征物,便于追溯和管理。也可能是我所不理解的什么逻辑,如果我能够理解,并且加以运用,我就不用做推销员了。我会成为一名拿年俸的尊贵绅士。”“你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公司要求,高层或许认为穿得像是从资本主义初期穿越而来,可以增加可信度,他们也许是对的,我看你多多少少明白了我说的话——也可能是更糊涂了。对于现在的顾客来说,资本主义初期,不就像创世之初的神话一般,那我们——”“天神下凡?”“或者说是‘穿上拖鞋’。”“你们怎么不穿明朝的衣服。”“试过的,然而放弃了。因为实在太热。”我被逗笑了,笑声像一千只鹦鹉一起振动鸣管。“好吧,这个故事最扯淡,但它也许是真的?”他摇摇头,“我编的,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没有正式工作,自以为是个作家的年轻人,不得不做了销售”,他很安静地喝完一瓶啤酒,用手帕将酒瓶擦拭干净,立在一旁。他有洁癖,或者有案底。他直视我的眼睛,“好了,说说你的问题吧,你今天坐立不安,我希望比冰箱要复杂。”我挠挠头,“的确是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妻子。”“希望她回来?”“恰恰相反。今天一早就有预感,她随时可能冲进家门,手里握着斧头或者格洛克,对我大吼大叫,再弄死我。”他点点头,“嗯嗯,毕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高度完善的阶段了,逻辑调转过来。需要给你一把冰锥吗?需要信用卡分期和十五年牢狱之灾,至少。我的方法,免费,这次应该不会再给你送鹦鹉了,或许是一只金毛犬。”“好吧,就再试一次。”“那么,有照片吗?”我从钱包里取出唯一的一张证件照,递给他。“她叫……”“不重要,我不需要知道,照片也只是看看,马上就还给你。”他看了约五分钟,然后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走到门前时,倒还没忘了脱帽敬礼。我失眠了,辗转反侧。他说的那些鬼话固然扯淡,但扯淡的事情还少吗。试一试,我也不会失去什么,对我这样毫无社会信用的人而言,可说毫无作为目标的价值,对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我是无关紧要的小小错误,能让自己舒服一点,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已可算是满怀怜悯的人道主义救助了。试一试吧,万一成功当然完美,若是失败——大概率,还有纳税人支付我的服刑费用。听说最近的监狱里,犯人们也像上班一样,打ColdCall,拼命推销产品。哪里都差不多,果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天,她没出现,我购买了一支黑枪。第三天,她没出现,我把通往二楼的楼梯堵死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给她的娘家和最好的几个朋友家打电话,得到的答复不可谓不惊悚,“坂道美瑠是谁?我不认识,你打错了吧。”放下电话,我忘记了呼吸,差一点将自己憋死。良久,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前院传来动物抓挠门板的声音,打开一看,是一只漂亮的萨摩耶,脖子上的狗牌上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写着:“祝单身生活愉快顺遂。”我抬起头,呼吸了一口混杂着腐臭味的新鲜空气,这可真是太他妈愉快了。房间的重新装修非常顺利,我把所有的钱都挥霍一空,砸重金为自己购置了家庭影院和游戏机。我还抽空去了市中心,的确如推销员所说,这里腌臜透顶,但开在地下室的那间机器人妓院还是不错的。我常常在街区里看见他,行色匆匆,看上去非常忙碌,我每次都和他打招呼,他就脱帽致意,动作越发娴熟优雅。街区的变化显而易见,一夜之间,养宠物这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被一些傻逼学会了。H总是牵着一条法国斗牛犬,像佩戴了一枚勋章。他的瘫痪多年的老母亲消失了,我想他也知道我的妻子是怎么回事,遛狗的时候,我们心照不宣地对彼此微笑,而不置一言。有一天,那个脑袋坏掉的小毒虫,骑着一匹白马从我的门前经过,我真担心他那副柴火棍一样的身体从马背上掉下来,再被马蹄踩碎了脑袋。街区尽头的那片垃圾场不见了,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解决的麻烦越复杂,牵涉的人、物越多,得到的动物就越大。用他们一家换一匹马,真是一个天才的想法。感谢上帝。但渐渐地,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同,因为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出现在了街道上。一天早上,我在浅睡中感受到脸上一片冰凉,伸手去抓,触碰到冰冷滑腻的东西,睁眼一看,一条森蚺瞪视着我。我想,至少周围的三个街区都听到了一个男人声嘶力竭的哭喊。这条巨蛇属于一个外地人,一个沉默寡言,总是躲藏在阴影里的老年男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究竟处理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抱走了这条蛇,连一句道歉都没留下。我还看见了一条科莫拉多龙,我怀疑它的主人并没有找怪人解决任何问题,他只是想尽办法,从黑市买了它,又把自己的妻子剁碎给它当食物。直到看到一头西伯利亚棕熊,我觉得事情可能是有些过头了。“早上好,推销员先生。”在又一次碰见他时,我主动打了招呼。“早,萨摩耶先生。”他的微笑显得有些疲惫。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但无所谓了,直奔主题。“最近的动物是不是有些奇怪?”“您是指基因变异的那种奇怪吗?”“有些动物恐怕不应该被当作宠物。”“或许。但既然我们都将一只脚站在了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之外的不毛之地上,恐怕也没有任何理由对有人饲养子弹蚁或食人鱼表示反对。也不能这么说,或许恰恰相反,我们正在深入资本主义的核心,那种自由自在、随意发挥想象力的交易关系。非要打个比喻,就像悬赏一个黑色头发、说纳瓦霍语、六个乳房的亚洲女人,只要你有交易的筹码,你一定会找到的,是不是很棒?”“话虽如此……”“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他急匆匆地走了,看来又是无比忙碌的一天。平平无奇的一段时光。我所说的平平无奇,是既没有破产,也没有暴富,还是吃三明治和肉罐头,还是喝水龙头里的净化水、速溶咖啡和冰镇啤酒,还是没有让资本主义体系骗走我的钱,也没有从资本主义体系占到任何便宜。说起不等价交易的奇迹,生平仅有一次,真是爽快。但时间一长,我的心里惴惴不安,我的等价交易的直觉告诉我,通常,弱势的一方被拿走更多,才是等价交易,比如用健康换金钱,如果弱势的一方还没有付出足够的代价,就拿到了交易的标的物,或许是因为对方有更大的陷阱,正等着我一步踏进去,比如,用消费贷买手机,不仅让我签了与小贷公司的贷款协议,还贩卖了我的个人信息。对此,我也多次询问过,推销员的笑容依然无懈可击,解释也颇为耐心,但我的顾虑依然悬在那里,无法消除。我现在是在见证奇迹,还是又一场骗局?我无法说服自己。直到我看见了一条龙。起初,只是漂浮在空中的灰色微粒,像云朵一般慢悠悠地漂浮在几个街区之外——商业区的楼顶上空,渐渐有了形状,先是一颗巨大的头盖骨,接着是脊椎、肋骨、翼骨,长而有力的尾巴,还有四肢。新闻节目推测是新修的本地地标——一栋一百二十一层的办公大楼的一次全息投影广告。我知道那是什么,尤其是当一片片血肉粘合在骨架上,筋膜构成的翅膀在缓缓扇动,我越发确信地知道。他的生意终于做到了富人区。或许是他的同事,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两个星期,那条龙就几乎成型了,偶尔能听到粗重的呼吸被北风送至耳边,还能看见它的鳞爪抓握着空气。是什么样的客户,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不禁好奇。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是不应该好奇的,但他们常常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就像忍不住拥有人性一样,所以他们是穷人。我抓住机会,问他:“我不问别的,就想知道那是解决了什么问题?”我指着那条龙。他看看我,问:“没有关心这种事的必要吧?”“得了吧,我敢打赌你们没有保护客户隐私的义务,不然我的事是怎么在街上传开的,若不是我,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找到你,也不会有它。我只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居然可以换到这种东西。”他看着我,面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也罢,毕竟喝了你两瓶‘虎牌’啤酒,就告诉你吧。最近的新大楼可知道?”我点点头。“一百二十一层,总裁就在顶楼办公,你可知道?”我摇摇头。“可知道他在顶楼能看见什么?”我又摇摇头。他朝东一指,“第五大街”,又朝西一指,“第十三大街”,“这八个街区的景色实在称不上好,因为……”“穷人太多。”“也可以这么说,他用的词要更为极端。他的想法是这样富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不应该被阁下……这样一群人占据着。“还有这样的房子”,他的手指划过整个街区,像上帝分开了天和地。张彰,80后,艺术学硕士。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有民俗学专著多部,并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著有长篇小说《青年旅社》。发表各类文字计多万。张精锐
还好有诗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renyua.com/tgjj/6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