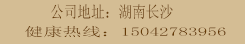文/孙亚西图/刘仲华
年生于重庆酉阳县。当过知青、编辑、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酉阳开始诗歌创作,同时与酉阳“莽汉主义”诗人一同混过漫长岁月。独树一帜,不需要“主义”,自称“野莽汉诗人”。著有自选自印诗集《遥远的钟声》、《怒吼》,长篇小说《敖哥》、《羊》、《在疯人院》、《爬满藤蔓的城堡》、《到天堂去》等五部(每部40余万字)。现暂居黔江热爱神学和科学。
第一次
一九九二年的天空很鬼,整个一年都在阴阳怪气地对着我冷嘲热讽……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呆着像一头困兽,那一年,我的脾气大得我无法驾驭,酒量深不可测……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朋友们去了酉阳后溪,那时正是夏季。
黔江地区行署的领导指派我和饶昆明写一个黔江地区成立以来的全面发展的专题片(政绩展示),我他妈从来都没写过那样要命的东西,这一切自然就推给了老饶,我就自由了。我说咱们去酉阳写吧去把李亚伟抓出来然后到后溪,老饶说:“行”!
到了酉阳,住蔡利华家。老饶说他要专心地写,写完后就去专心的耍个痛快。老饶责任心极强,我依了他。于是老饶就躲在蔡利华家写。我说老饶你就安心地写吧,我和老蔡烟酒茶都给你备上了,不影响你做正事我们出门去看风景去了……
到了李亚伟家。我看见亚伟在练毛笔字在学许国璋英语在看弗雷泽的《金枝》。(那时亚伟才从狱中出来不久,在家无所事事。)我说别再学习了我们现有的文化足可对付这个世界和我们一起去后溪乐几天,亚伟欣然同意并说行是它妈很久没开笑脸了力比多憋得老子难受是该找个地方释放释放了……
快到晚饭时老饶就把那个专题片的脚本写完了。他叫我看看,改改,我说不看不改,你老饶写的没有什么可改的,一改就坏了,党和人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彻底放心!老饶嘿嘿直笑。蔡利华说走走走去馆子喝酒。来到一个渣渣酒店,除老饶不胜酒力,我们都喝得无法无天。老饶说都别喝了咱们明早还去后溪,老蔡说就最后一杯,喝了就躺着睡觉明早好上路。
第二日,我们坐上一辆陈旧的客车上路了。蔡利华没去,他要上班。客车只开到酉酬就返回,留下的去后溪的路就全凭自己解决了,这出乎我们的意料。
此时正是中午,天热得像卵形,我们在酉酬的街上转悠,打听去后溪的车,然而根本就没有去那里的车(那时车马稀少,尤其是乡下),我们在那里又举目无故人。转了好一会儿我感到我们中天计了,进退不能,被荒山野寨包围了,遍坡草木皆兵,逼得我们走投无路。这时我们感到了饥饿,围在一个土灶旁吃土家油粑粑。那东西实在好吃,我想给英国女王捎几个去。我们边吃边吹牛屄,快活起来就忘记了困境,那些土家人站在一旁嘿嘿直笑。我说:“听以前杨长江说后溪场上有一刘仲华,是一介隐儒,好三教九流之人,在大山里已经成精了,我们此去一定去拜访他……”话音未落,一个青年小伙子拨开那些看我们的人,对着我们说:你们是城里来的?找刘仲华?我们说是是是,是去后溪找他,他说你们没有找到车?我们说哪里找呀?他说别急别急,先到馆子里酒足饭饱后我给你们找。我们发现他完全是个bai子,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在我们看来棒极了!我想,如果再有一个瞎子和一个断臂的和我们在一起就更棒了。
那青年bai子姓蒋,我们就叫他蒋bai子。
蒋bai子把我们带到一个苍蝇小店里坐定后,立刻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店主说:“这些都是我的贵客,城里来的,你想法去弄两条蛇来炖起,然后炒些好菜来我们下酒!”店主立即跑去找蛇去了。狗日这个蒋bai子还真看不出有如此侠义,我突然对他产生一种亲密的哥们之感。
一个时辰后我们酒足饭饱,蒋bai子就给我们找来了一台手扶式拖拉机,他说:“实在没有其它的车了,若有,我一定会弄来的。”我们面面相笑,我说:“行,只要能到后溪。”亚伟说:“上车吧,我们就是要坐这台拖拉机去检阅祖国的山水。”蒋bai子在一旁嘿嘿直笑。我说老蒋你也上车吧,他说你们先走,我骑摩托。老饶知道拖拉机后箱很抖,就把我和亚伟赶到了后箱,自己就嘿嘿笑着坐在驾驶师傅身旁。
拖拉机发出嘣嘣啪啪的怪叫上路了。
拖拉机跛去跛来的急抖,我和亚伟在后箱里直站着两手紧抓住铁架,我说这路真要命,身子骨都快抖垮了,这还算路吗?亚伟说这样安逸,比坐飞机强多了。我说我感到我们又回到了七十年代。亚伟接着说,是,我们坐上了一辆历史的倒车,正在向古代开去。我说是呀,沿途我绝不下车,我要去唐朝,去尝尝肥美的杨贵妃。亚伟笑着脸说,我要去宋朝,去宋朝的酒馆,写一些伤感的宋词,然后拿到唐朝去发表。我说,你狗日想引起唐玄宗的注意,把你招进宫里好伺机与杨贵妃勾搭,和我争宠?我俩哈哈笑起来。这时老饶在驾座上说,你俩在笑啥?抖舒服了?我大声说,抖舒服了!抖进了杨贵妃的怀抱了!拖拉机师傅也嘿嘿地笑着说,你们真会开玩笑。
这时我看见一个小丘陵上有一幢倾斜得很厉害的木瓦房,估计倾至45度,岌岌可危。我说,亚伟,快看那房子,比比萨斜塔还要厉害。亚伟说,它在寻找风。我说,它在追求风,想逃。我俩又笑起来……
拖拉机摇摇摆摆终于摆到了后溪。我们在后溪场上打听刘仲华的住处,一个老者指着一幢漂亮的老木瓦房说:“那里就是。”
我们向刘仲华的家走去,看见有几个病人在那里输液(后来才知道是刘仲华在家里开的诊所),我问站在门面前的一个妇女:“请问这是刘仲华家吗?”妇女答:“是,你们来看病吗?”我答:“我们没有病,是杨长江叫我们来找他的。”妇女哦了一声明白过来,立即转身进里屋去把刘仲华叫了出来。我说我叫孙亚西,他叫饶昆明,他叫李亚伟。我们是杨长江介绍来的。”刘仲华一见如故地说:“啊呀,贵客!贵客!你就是李亚伟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你就是孙亚西呀?我们以前在一条街座,我知道你!”我向他介绍说:“这是饶昆明,作家,写小说的。”他激动地说:“老婆,快把饭煮起,把我那坛老酒搬出来,今天来的是贵客!”他老婆就愉快地煮饭去了。
(我记得刘仲华当时有两个女儿——或者三个?其中一个叫文岱?记不清了。)我们正聊得兴致之时蒋bai子到了。蒋bai子的到来又增添了几分喜悦。
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下蒋bai子:蒋bai子是酉酬城里社会上的一霸,结三教九流,重义气,头脑精明,酉酬片区社会上的混混都知道他的鼎鼎大名,敬畏三分,老蒋对真正的文化人特别感兴趣。
刘仲华的老婆(之后我们就呼嫂子了)做好了饭菜,刘仲华说,走,喝酒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在刘仲华家住下了。蒋bai子一直陪着我们。我们都似醉非醉,老饶独自清醒。
我们胡乱地谈古论今,蒋bai子在一旁津津有味听出了口水。这时我提议唱山歌,大家一致赞同。我首先拖声迈气地唱起来——
太阳出来噻红又红,骡子鸡巴呀戴斗蓬。
太阳出来噻翻过坳,骡子鸡巴呀戴草帽……
大家哄堂大笑。笑毕,突然屋外传来真正的山歌声,那歌声原滋原味振聋发聩,仿佛来自世外之音!我们都无声地竖起了耳朵!什么帕瓦罗蒂、莎拉·布莱曼、迪翁,在我听觉的记忆里突地凄然失声!我们急向窗口望去,发现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刘仲华说他听见我们在唱山歌,是来挑战的。听刘仲华这一说我们谁都不敢再唱山歌,改唱了流行歌曲。亚伟抱着吉它叮叮咚咚地弹……
翌日,太阳升起了老高我们还在呼呼地睡。嫂子对刘仲华说早饭就快变成中午饭了你快去叫醒他们,刘仲华说让他们睡他们都有睡懒觉的习惯。
终于老饶第一个醒来。他醒来就故意拉大嗓门唱山歌,把我们统统吵醒了。这时刘仲华笑着脸走来说:“早饭就变成午餐了,你们都懒得像卵形了。快起床,吃了饭我去弄一条船去漂酉水。”
饭后老饶说他的相机的胶卷用完了,刘仲华说这地方没有那东西卖,亚伟突然说:“去找胡世发,他是我的亲戚,在这镇上当镇长。”于是我们就去政府衙门找。
政府的人说胡镇长在外学习去了。亚伟想了想说:“我认得这里学校的一个老师,去找找他。”我们去那学校果然找到了那个教师,并从他那里借到相机和两个胶卷。我们返回场上时看见土家人那些油粑粑,嘴又开始馋了,我们围在一个土灶前蹲着慢慢品吃。这时一个瞎子白胡须老者坐在那在给别人算命。我说,亚伟,我们找他算一卦如何?亚伟说算算看。
那瞎老先生把亚伟的头摸了手摸了(就只没有摸屁股了),然后再叫亚伟说出生辰年月。亚伟报出生辰年月后瞎老先生曲指算起来,突然说:“此命露牢狱之灾,但已过,算来此命大贵,可至百万不等,但切莫在家与父母兄弟长住,否则克他们。向西北发展落住,富贵自然,后无大忧。”我们在一旁听神了,因为先生所言击中亚伟命迹!我们感到此老就是神仙下凡!亚伟即向老先生付了算命钱后问我也来一卦如何?我说不算不算我这条命深不可测。这时刘仲华赶来催我们去码头上船。
我们坐上一条木船,刘仲华向艄公说:“就从下漂,漂到长潭去洗澡(游泳)。”
我们就坐在木船上漂啊漂啊,真想漂出这个世界……
经过若干激流险滩,我们终于没有漂出世界却漂到了长潭。
我们拔光了衣裤赤裸裸跳进长潭的水中,舒服极了!很久都没有到野水里这样游玩了。这时刘仲华在岸上大吼道:“当心食人鱼咬鸡鸡!”老子听后吓了一跳(用词不当?水中不能跳),我边游边大声向昆明和亚伟喊叫:“快向岸游,有食人鱼!”
我很快游上岸来,然后亚伟和昆明也上了岸。
我问刘仲华:“怎么这里有食人鱼呢?”刘仲华笑着脸说:“听老古邦人说的。”
我们看出刘仲华的作态,明白是他在有意戏着玩。饶昆明笑着说:“如果有那种鱼,我们的鸡巴早就不见了!”我们笑了片刻后昆明又说:“照相合个影。”刘仲华举起相机,照出了我们赤裸裸的合影。
在水里尽兴之后我们穿上衣裤随刘仲华就向长潭的街上而去。这时我突然发现一美貌女子坐在一架缝纫机前缝纫衣服。我们走近她,她就越发美了。这时刘仲华和她随和地说了一些家常话就把我们带走了。严格地说,我看上了那女子。我想和她生一串孩子,与她在这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欢度一生,我要把我们的孩子起名为:铁蛋、铜锁、灰二、丘八、豌豆、胡豆和小狗腿子,我要在家中称王称霸,率领孩儿们在酉水河上打鱼摸虾……
刘仲华突然问我:“你在想啥?”我说我看上了那个缝衣的女子,我想娶她。他嘿嘿直笑说你在开玩笑呀,你怎么能娶她呢她不过是一村姑。我说我就喜欢村姑。他说别开玩笑了那是一辈子的事!我说我不开玩笑我就想娶她。刘仲华说,你狗日还来真的了?那我回头去问问她。
刘仲华问她去了。
片刻后刘仲华就返回来说:“她已经有人户了(订婚之意)。”老子听后一身都蔫了。刘仲华继续说:“我有个远房亲戚,比她更漂亮,我以后为你联系。”我只好虚与委蛇地说你就联系吧……
我们返回后溪场时天已近黄昏。我说再去街上转转买些土货带回。转了一趟,我们每人都买了一双草鞋搭在肩上,慢吞吞地向刘仲华家走去,街上的人都带着笑脸望着我们,我们仿佛成了他们眼中的疯子。
第二日,我们坐上了一辆世界上最糟糕的客车,走了……
第半次
时隔十五年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喂喂,是孙亚西吧?”我说当然是。“过来过来,和我们一起到酉水河去吃鱼——我是张万新,文林也在酉阳,还有新疆来的朋友何念尚——过来啊——我们在酉阳等你!”
第二天我把许显昌也拉了去。
我们到了酉阳就去我们另一次住的那地方把文林找到了。那地方不是对外的宾馆,是一个单位的内部招待所,有一次我们和梁乐也是住这里——因为梁乐的妹在那单位上班。文林说这次是来采写关于大湘西的文稿和拍照,(当时文林在主编一个《中国地理》的杂志。)并向我与显昌介绍了何念尚。我问,张万新呢?文林说还在他家里睡觉。我说他狗日就是爱睡懒觉,听敖哥说他就是懒,不然早就去当中国作协主席去了!许显昌说,快快,电话把他催出来一起去喝酒!
电话打去后不久他就来了。他一进屋首先就冲我说:“狗日终于把你催来了!”我笑着说:“我也是同一句话给你——狗日终于把你催来了!”许显昌说别再吹了找个地方吃饭喝酒去。待文林关完笔记本电脑和拔完插头后我们就到一个拐角处的餐馆喝酒吃饭。显昌不喝酒,念尚喝少许,文林要驾车也不喝。剩下喝酒的就我和万新了。我说,咱俩就喝吧。
我感到酉阳的枸杞酒度数有些高,才半斤酒下肚嘴里就屄话超过了文化。我说,万新,还喝吗?他说算了算了不喝了这鸡巴酒有些厉害。我说我也有同感,这酒里是不是下了药?有一年我与况洪波和张昌一大帮人——冉仲景有事先逃了——全喝翻了!后来才感悟到酒里下有什么毒药。狗日今天这酒里也肯定有。这时文林说算了算了,被老板听见了伤和气。酒足饭饱后我们就回寝室打牌吹牛……
第二日我们按计划去后溪。去之前万新已打电话给他在酉酬的哥们喻连河,说把鲢鱼和酉水豆腐煮起,我们马上从酉阳出发。
我们坐在文林的小车里一路上顺当当地到了酉酬。喻连河早就等着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饭店里,把早已准备起的鲢鱼抓出去杀了。我们开始喝酒吃鱼了。席间我说,万新,把你那条马口鱼也拿来煮起,看是啥鸡巴味?!万新嘿嘿直笑说,那鱼还咬着鸡巴没松口呢!
舒舒服服地吃完鱼喝完酒后我说走吧到后溪,到刘仲华那里,刘仲华那人是这个世上最好耍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他耍过,那就是一个不丰富的人生。显昌说,先给他打个电话去。我说没有必要,搞他个突然袭击更来劲。我们坐上车,向后溪开去。
路非常难走,沿途在整修公路。我们几个大男人快要把文林的小车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完全是一种强奸的势头。
车行二十多分钟后停了下来再也开不动了。文林开始检查,搞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原因,于是就打电话给在酉阳的李亮(李亚伟的小弟),叫他和汽修站的师傅联系,开辆拖车来把车和我们一起拉回酉阳。于是我们就无奈地等,就无聊地等,就傻乎乎地等,然后就开始抱怨这鸡巴车质量差,这鸡巴地球也坑坑洼洼……
时至黄昏,从电话里得知,那拖车才从酉阳出发!我操!在这荒山野岭,我们就像是被祖国抛弃的人渣。我们此刻是那样的无助,是那样的落寞,又是那样地可笑,可怜!我大声说:“同志们,天马上就要黑了,等那鸡巴拖车开来时我们早就被一群女鬼带走了!”大家无奈地嘿嘿笑了笑。这时山风吹得荒草嘘嘘作响,夜,说来就来了。我们只好又钻进车里关好车门埋头睡觉。这时文林突然说大家睡个卵啊,打起精神来,现在我们来吹敖哥。
一提起吹敖哥我们就有话说了,敖哥的故事已深入我们的内心,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那狗日一辈子都出人意料,深不可测……
我们在车里一阵阵的大笑,在这荒山野岭的黑夜里,如果被其他的人听见,还认为真的碰上鬼了!
拖车终于来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仍然坐在小车里,小车坐在拖车上,就那样把我们拉回了酉阳城……
这就是我说的“半次”。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renyua.com/tgjj/74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