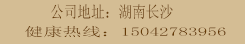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我的一生。我是一个普通人,但又取得了一些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就。这么一想,似乎每个人都是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小区门口卖包子的大爷,从我记事起就在那里,而我现在都已经半头白发了。能坚持这么多年,我很难说他是普通人。而且,他的羊肉包确实好吃。没有办法,为了和其他人能有所区别,我只能把我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不普通——普通——不普通——普通。
我的人生记忆是从六岁第一次上学的那天开始的,而在这之前的五年,于我而言只是个混沌的梦。梦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玩具恐龙,没有声音,甚至连颜色也没有。它比真空要安静得多,而如果要找个颜色,也很难在世界上找到能盛放住它的调色盘。我在这个混沌里飞来飞去,困了好久,只是偶尔能够看到一些突然出现的模糊的画面,听到一些遥远的呓语。画面扭曲而闪现,却是我在混沌中仅有的乐趣。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初见时的欣喜,就像虔诚的教徒终于得以窥见神的旨意。尽管我只能回想起一幅画面的一角,并隐隐觉得那团绿色应该是一棵春天的树。至于声音,我从未听清过,只觉得那微弱的呢喃来自宇宙的深处,或者来自某个民国时代的电报机,时断时续。
在那个和往日一样寻常的夏天,妈妈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小学。蝉声跟着我们,灰色的石板铺满了院落,从梧桐树叶间透过的光影熙熙攘攘,照得石板一地斑驳。见有些晃眼,我就用手挡在眼前,但还是忍不住松开手指,眯着眼抬头看。光影摇曳间,我仿佛听到一声鸟的鸣叫,高亢而威严,叫得我脑袋一颤。妈妈拉着我继续走,我扭头仔细看了看,树上好像没有鸟,只有蝉。
喧闹声的尽头,就是一座教学楼。当我和妈妈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教室里的声音就渐渐安静了。老师走过来跟妈妈打招呼,所有人都望向我们,但我觉得是都望向了我。第三排最右边的那个穿蓝T恤的小男孩,刚才还在尝试拔前桌女生的头发,现在也和那个女生一样,直直地望着我。明明刚从太阳底下走到阴凉的地方,我却更热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化作麦芒,在我的衣服里从上到下游走,我努力挺直身体,却浑身发抖。
“妈妈!我们回家吧!”我带着哭腔喊出了人生的第一句话。这一刻,我觉得脑袋里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我会说话了,在一个丢人的时刻。妈妈跟老师嘱咐了几句,就带我回家了。爸爸没有因为我第一天上学就逃跑而说我什么,相反,他和妈妈挨个给姑姑舅舅们打电话,似乎要普天同庆。晚饭很丰盛,爸爸要我再给他多说几句话,我说快吃吧,别说话。
在我三岁时,爸妈终于医院,医院检查我的生理器官都正常,但这就让人疑惑不解了。很大几率上,他是能说话的,可能就是单纯的说话晚,也可能是心理问题,不如再带他检查下心理。医生这样跟爸妈说。而心理医生要么说我极度内向,要么说我是自闭症,因为我总爱一个人呆着,不哭不闹,拿着玩具恐龙在水盆边上玩。绕来绕去,爸妈接受了现实。他们的儿子,一切都还算正常,就是不会说话,有点内向。现在好了,只剩下内向了。
当晚我也很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晚饭很丰盛。我的梦里终于不再是混沌的一片,那个困了我五年的屏障似乎随着我的哭喊碎掉了。我漫步在下午去的校园里,没有妈妈陪我,也听不到其他孩子的喧闹。但我能清楚地看到绿色的树,感受到毒辣的日光。灰色的石板上有蚂蚁在爬,它们围着洞口进进出出,背部像滑梯一样光滑,脚上沾了点灰尘的绒毛也清晰可见。我甚至能感觉到这片院落里有多少蚂蚁在发出脚步声,那需要好多好多个10加起来。六岁的我,数学水平还不足以将那个数说出来。混沌中的梦呓也终于被蝉声所取代。我跑到梧桐树下,抬头去瞅树上的那几只蝉。我看到它们的肚子一鼓一鼓的,一秒钟里鼓了好多好多个10次。我盯着其中一只,恍惚间觉得它似乎出生在五年前,今天是它变成蝉的第三天。这时,随着一声穿透云霄的啼鸣,天暗了下来。
庞大的阴影遮天蔽日,流苏般的尾巴燃烧着熊熊火焰,我的梦都笼罩在这只鸟的身躯下。蚂蚁停下脚步,蝉沉默不语,树叶寂然不动,整个校园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而这只鸟一振翅,洒下漫天飞羽,片片光芒在我的瞳孔中绽放又熄灭。片刻,它落到梧桐树上,太阳重现天空,整个校园又开始了运行。我数了数蚂蚁,一只不少;听了听蝉鸣,节奏没乱。我望向这只鸟,它也望着我,明晃晃的眼睛里似乎充满着跟我一样的好奇。全身通红的鸟我从没见过呢,而且刚才那么大只,怎么变这么小只了。我试着去感受它的来历,我的思维却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潭水,那里面一片漆黑,思维扑通一声溅不起任何涟漪。而在刚才,我明明看到了那只蝉的一生的。再次集中精神,我把注意力放在掠过树叶的风上。这阵风来自一个广阔的海洋,它裹着海洋的咸味和海鸥的声音,在漫过一群小岛之后,夹杂着粉色的花香翻山越岭来到了这里。所以掠过脸庞的还有小石子跌入山谷的回响,高速公路上飘动的浓雾,断了线的风筝,以及一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最明显的,是学校食堂里青椒炒肉的油烟。
我能感受梦里的一切,却难以窥探这只鸟的一丝一毫。或许,它是我的梦外来客。
我正要跟这只鸟打声招呼,就被妈妈喊醒了。她先让我喊她一声妈妈,确认我还能说话后,她告诉我今天必须去学校。我用被子蒙住头,喊着不去不去,可我到底还是在几次哭闹无果后坐在了教室里。奇迹般地,当所有人的目光望向我时,我不再发抖和出汗,甚至还出于本能地报以微笑。那个昨天试图揪前排女生头发的蓝衣男孩主动申请成了我的同桌,笑嘻嘻地坐到我旁边。老师讲的东西我听不太明白,我也就没仔细听。蓝衣男孩也不听,他教我怎么悄么声地揪女生头发,怎么折能飞回手里的纸飞机。我学得很快,当天就被女生告状了。老师训了我一顿。我也不再内向了。
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踩着两个黑板擦在黑板上滑行,把老师写的满满一黑板的字擦得干干净净。那个告状的女生又被我和同桌拔了两根头发,急得直哭。我告诉她说,你别哭,我给你变个魔术。我把那两根头发搓成一条,往地上一扔,缠绕着的藤蔓拔地而起,越长越高,越长越粗。我们跳到叶子上,一下子就到了云端。藤蔓在云层上打了个结,顺便开了朵花。在云上玩腻了,我让同桌折了个纸飞机,我们一人抱团云朵吃着,坐上纸飞机又飞回人间了。云朵甜甜的。
从此,我终于变成了正常人,至少在我睡觉前是这样。而每到夜晚,我就是我梦里的神明。白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晚上我就能在梦里和它玩耍,牵着毛线团勾引它跑,我们能跑好多好多个10米。妈妈有时候会因为我在学校捣蛋不给我买玩具卡片,我就会在梦里下一场大雨,不过下的全是卡片。如果这些卡片是真的,我在学校比卡片是一定不会输的。有次我在书上看到一只虎鲸跃出海面的图片,于是我当晚就在海里来了场探险。我骑在虎鲸的背上耀武扬威,四处寻找着鲨鱼群,然后让虎鲸冲进去打滚。看到鲨鱼惊慌逃窜的样子,我无比开心。刚想夸一下这只海里的熊猫,我就看到一艘深蓝色的潜水艇在前方行驶。它像幽灵一样静谧,我竟然没有感知到它的存在。里面是谁,它怎么能和那只鸟一样,肆无忌惮地进入到我的梦里来呢?我让虎鲸加速,但还没靠近,潜水艇就不见了,像是从没来过一样。我以后再没见过它。
那时候某个电视台会在夜里放一些或悬疑或恐怖的片子。好巧不巧,爸爸在我睡觉前没有换台,我一个小孩正好目睹了一个人掉入水中,被食人鱼啃食殆尽的场面。同桌说到七岁就不是从前的小孩了,于是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嘴巴不喊出来,但还是压制不住奔跑的心跳。躺在床上,我一闭眼就是那具白骨。好不容易睡着后,白骨还是出现在了我的梦里,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鱼腥味。我吓得忘记了我能掌控这里的一切,在小船上无助地哭泣。白色指骨的寒冷离我越来越近,我缩成一团,祈祷着离开这个地方。鱼腥味突然消失了。我站在校园里。蝉还在鼓着肚皮,蚂蚁仍旧忙碌,来自海洋的风没有停下脚步,那只鸟在梧桐上盯着我。
你好。我朝那只鸟挥挥手。它歪头愣了一下,叫了一声,学着我挥了挥右翅膀。有意思。我很高兴,想飞到空中离它近一点,却被闹钟给惊醒了。带着被吵醒的烦闷,我给爸爸讲述了梦里的鸟。他说,《庄子》上记载,有一种鸟叫鹓鶵,只在梧桐上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好喝的泉水它不喝,跟你一样挑食呢。我嘿嘿直笑。爸爸接着说,鹓鶵是黄鸟,你梦到的是红鸟,但它们都是凤凰。梦到凤凰代表我们家小子要交好运喽。他把我举起来想要转圈,妈妈说别闹,快吃饭。
接下来这几夜,我做了个实验。我在一片红色的湖边钓水怪时,默念着离开这里;在珠穆朗玛峰上制造雪崩时,想着离开这里;作为指挥官快要取得战争胜利时,我也想了一下离开这里(尽管这个念头给了敌军喘息的机会,最终造成了我军的溃败)。不出所料,无论我在梦里干什么,只要我想一下离开这里,就会回到有凤凰停留的那片校园。我猜测,我脑子里原本停放着混沌的地方,在破碎后被我第一次梦到的校园占据了。这片梦中的校园就是我的基地,而我的其他梦境就像是一场场匪夷所思的户外探险。每当我想回到基地,连回城咒语都不需要念,只要想一下就能回来了。有一点不妙的是,基地我每晚都能见到,但那些奇妙的户外冒险却是一次性的。我能梦到什么,全凭天意。这一点很像我看的动画片《马丁的早晨》。
每次回到基地,我都不会闲着。听了爸爸的话,我扩大了基地的范围,种起了竹子。我当然可以凭空唤起一片竹林,但基地我想好好经营一番。种了几株竹子后,我突然想到我是挖不出来泉水的。放下铁锹,我一抬手,一汪蓝白色的泉水就咕嘟嘟冒了出来。我招呼凤凰下来。它左右歪头,似乎忍不住诱惑,最后还是飞下来了。它一口就喝掉了半池。我目瞪口呆地给它续满,续了几次之后,它终于像是喝饱了,看我一眼,又看看竹子。我明白了。于是一片竹海也拔地而起。同桌说过,人是要懂得变通的。所以,我自己种竹子和直接变竹子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从天上摘了点云朵吃,凤凰则在竹林里吃的沙沙作响。吃完过后,我俩在梧桐树上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看着夕阳将晚霞拖入黑夜。
我跟凤凰成了朋友了。每次我从别的梦境中冒险回来,就会在基地里陪它吃饭。我告诉它我刚才在跟霸王龙赛跑,而昨天我在热带雨林的游泳比赛里赢了鳄鱼和蟒蛇。我告诉它爸爸妈妈今天吵架了,问它我为什么总是考不好。它不会说话,但有在认真听。蹦起来在空中挥舞翅膀,那是它兴奋的样子。发出狗狗撒娇时的低鸣,用头蹭我的衣服,那是在安慰我。有时它会变成初见时的样子,让我坐在它背上,冲出我梦境的天空,在宇宙里遨游。无数的星辰从我们身边掠过,烦恼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我们不断飞行,见证了遥远星系在爆炸中壮丽地毁灭,也目睹了一块陨石上生命物质的诞生。
时间转眼即逝,在凤凰还是如初见般那副模样时,我却已经要大学毕业了。这个三本是我费了老大劲儿才考上的,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不好,我甚至到了门门重修险被退学的地步。而我不仅在学习上没天赋,在其他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在爸爸妈妈的怂恿下,我曾经学过画画、书法、钢琴、架子鼓……但无一例外,我都是班上孩子里学得最差的那一个。我画的荷花歪歪扭扭,像一团颜料糊在一起,同学都说是鬼画符,但我在梦里却能画出比莫奈的睡莲更神秘的花。我的睡莲由一小方蓝色、一小块长方形的粉红色和一丝黄色组成,水上的绿藻托着它,清晨的薄雾触摸它,熹微的晨光怜悯它。最后一笔画完,我的梦境里全是花开的声音,惹得湖水心神荡漾。我真想把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叫过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然后对着同学的画挨个吐口水。我的乐器,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发出塞壬的天籁。这声音曾把凤凰迷得从梧桐上跌落下来。如果梦和现实交换一下就好了,我想。
临近毕业,爸爸跟我说,想让我再考一次研。当时我正在处于迷茫的焦虑之中。考研失败了,找的工作也全都把我拒绝了。我似乎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技能,也学不到什么本事。我对爸爸说,不考了,我考不上。说完我就回到房间里躺着。爸爸在客厅里冲妈妈吼着我的罪状,一天到晚就知道憋在家里,这都多大了,考研考不上,找工作找不到,以后也是一事无成。我用被子捂住耳朵,不想听到母亲哭泣的声音。
那段时间,我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我反复梦到我在2月26号那天查着考研成绩,也经常梦到面试官问我在系里的排名。醒来后,我浑身是汗。凤凰也察觉到了我的焦虑,它在空中给我跳舞,它带我在宇宙里越飞越远(也许有一天,它和我能探索到宇宙的尽头)。我很感激它,但它这样做似乎起到了反作用。我在梦里言出法随,呼风唤雨,但当我醒来面对无奈的现实,我就像在安赫尔瀑布航行,那种巨大的落差随时都要将我生命的小船倾覆。以前我总爱在梦里幻想些有的没的。现在,一入睡只能感到现实的沉重。
一天,我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一位初中同学转发的筹款消息。我点进去一看,发现是我小学同桌的筹款。他得了白血病。我赶紧给这个初中同学发消息,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小学同桌。小学毕业后,我们因为去了不同的初中,就失联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不就是第一天上学就哭着回家的乖宝宝吗。我们聊了很久很久,倾倒着这些年的苦乐。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了。他说还行,就是有点疼。
那天晚上,我又梦到了我踩着两个黑板擦在黑板上滑行,然后我和同桌拔了告状女生的头发,我们三个顺着头发长成的藤蔓飞到云端,又坐着同桌的纸飞机飞回人间。醒来后我泪流满面,我从未如此迫切地寻找纸和笔,来把这美好的梦境记录下来。
之后,我随便找了份工作,一个人住着,每天和公司里的人一样朝九晚六。我的梦境终于有所好转,虽不像小时候那么疯狂,但终于不再被阴霾笼罩。凤凰也比以前开心了,饭量大了不少。从我和同桌再次相遇那天开始,我把自己这几年的梦境一篇篇记了下来,并称它为《梦境记录》,尽管我的语言描绘不出我那亦真亦幻的梦的万分之一,但我还是尽力还原它的一草一木。闲下来的时候,医院看望一下同桌。他的情况根本没有在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renyua.com/tgjj/6049.html